
]article_adlist–>
面对智能硬件应用爆发,各路风险投资机构群聚深圳抢夺关键项目,从硬件大厂到创新孵化,再到24小时运转的供应链工厂,盟约与算计交织,突破与跟风并行
文|胡苗 刘以秦
编辑|刘以秦
2026 年 1 月初,深圳南山科技园的 inno100 智能硬件集合店里,人头攒动。
货架上清一色是海外热销的 “ 深圳爆款 ” :外骨骼机器人、 3D 打印机、 AI 玩具、无人机 ⋯⋯ 或是出自大疆、小米、华为等巨头前员工之手,或是由本地供应链几天内打样迭代而成,件件都是这轮 “ AI 硬件 ” 热潮的代表作。
深圳一家头部风投机构的投资人徐清站在一款名为 “ 清闲 ” 的智能办公椅前,反复试坐了三次。椅子能自动调节腰托、监测坐姿,甚至通过微震动提醒用户起身活动。他眼睛发亮, “ 这产品我们真想投 ” 。
但很快,他的表情又黯淡下来, “ 高瓴刚投了它们 ” 。这个项目徐清跟踪了几个月,美元基金一来,他就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,项目的估值几个月便翻了倍, “ 我们连尽调名单都没进 ” 。
2025年的深圳智能硬件市场,宛如一个高速运转的造星工厂。
大量美元机构涌入,创业公司估值水涨船高; “ 大疆系 ” 创业者群体崛起,各类细分场景的硬件层出不穷,以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智能硬件产业,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球的品类重构。
这是 “ 深圳速度 ” 第一次如此具象地体现在创投领域,过去几年风险投资在深圳不算活跃,知名机构和投资人更多聚集在北京和上海。 一位深圳的 FA (财务顾问)提到,现在但凡有大疆背景的创业团队出来,从种子轮融到 B 轮往往只隔三四个月,价格翻倍是常态。
这一轮投资深圳的代表性机构是红杉中国,红杉决策最快速的项目,从接触项目到下 TS (投资意向书)仅需两三天。有些美元机构甚至可以现场拍板决策,当天打款。一些市场化的人民币机构也在积极参与,他们必须用 “ 美元风格 ” 来做投资:更高的估值、更快的决策效率。
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数据显示, 2025 年深圳共有 77 家具身智能及相关智能硬件企业完成 106 起投资,同比分别增长 51.0% 、 79.7% ,披露投资总额约 100.49 亿元,较 2024 年翻了近 7 倍,成为国内智能硬件投资最活跃的区域。
这场发生在本土的资本盛宴中,深创投、高新投等深圳 “ 土著 ” 机构却集体缺位 —— 它们手握地利、背靠政府资源,却眼睁睁看着外来的投资人们包圆了 “ 大疆系 ” 等优质项目,自己只能沉默旁观。
在一家深圳本土国资机构工作的王乐(化名)去看项目,创始人直接说, “ 你们流程太慢,等你们走完内部会,我下一轮都融完了。 ” 对于这些深圳本土投资人们来说,现在市场上项目分两种,一种是被美元基金抢的,一种是被剩下的。他们基本只能看后者。
故事的另一面是,过去几年,美元机构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 “ 存在感 ” 持续变弱。 早在 2021 年,就有不少投资机构不再募资美元,转向人民币投资。创投数据服务商 IT 桔子数据显示,过去五年,美元机构的投资总额减少超 84% ,从 2021 年的 5329 亿元降至 2025 年的 827 亿元。与此同时,人民币机构的市场份额从约 64% 涨至约 90% 。
在这背后,是两类资本从基因到玩法的根本不同:美元机构喜欢高增长、有爆发潜质的 C 端赛道;本土机构则更重视高端制造、国产替代等投资主题。过去几年,美元机构的投资方向大幅缩窄,不少美元机构都设立了人民币基金,甚至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投资,深圳的消费硬件崛起,让美元机构们再次展现出活力。
两种投资力量交织,从深圳本地的硬件大厂,到南山孵化器的路演现场,再到 24 小时运转的供应链工厂,盟约与算计交织,合作与博弈并行。
硬件投资“闪电战”
在 2025 年末的一场饭局上,投资人李永明(化名)与一干同行推杯换盏。席间某投资机构的投资人成为了焦点 —— 他所负责的一个智能硬件项目已经过会。
大家纷纷祝贺他,但一通电话结束了这次热闹,李永明看到这个投资人的脸色瞬间煞白。
就在饭局进行的时间里,另一家头部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带着团队直奔项目方公司,在该机构估值基础上直接加价 20% ,还当场签下排他协议。
创始人打电话来婉拒了他的投资。对于早期项目来说,真金白银的诚意和闪电般的决策效率,远比 “ 过会未打款 ” 的承诺更有吸引力。
在 2025 年下半年的深圳智能硬件市场,几大头部风投基金开启了贴身肉搏。
在 12 月时,李永明听说,一个从大疆离职的团队要做 CNC (计算机数字控制),还只有项目策划书,便拿到了某家头部机构 2 亿元的估值认购。而在 1 月中旬,他得知,那个项目的估值已经被另一家机构提高到了 1 亿美元,硬生生把价格抬了一个档次。
一家人民币机构的投资人看中了一个消费硬件的项目,但创始人已经拿了一线美元机构的 TS ,他加价 30% 才拿到投资额度。他投资的另一家消费硬件的项目,有其他机构当场加价 70% ,最终说服创始人增加一轮融资。
估值不断被推高的原因,是消费级的智能硬件终于能讲“故事”了。
深圳的消费硬件一度在美元机构投资人眼中等同于 “ 没有故事 ” 。华强北的生态太过强大 —— 一个创意、一张图纸,不出三天就能被拆解、模仿、量产。亚马逊上成千上万的 “ 大卖 ” ,不讲品牌,只拼供应链效率和流量运营,靠白牌产品赚取全球市场的微薄但确定的利润。
这是一门 “ 生意 ” ,能赚钱,但对人民币基金而言,没有技术的门槛和壁垒,也不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;对美元基金而言,讲不通抢占流量和未来的故事,只能算成本、毛利和出货量,很难有想象力。
但 2024 年后,深圳的智能硬件不同了。新一代硬件不再是简单的功能集成,而是 “ AI+” 的智能体。以软件定义硬件的模式,构筑了华强北难以复制的护城河。再加上立足于 “ 出海 ” ,这些品牌在海外市场获得了不错的利润。
创业者也不再是草根老板,而是来自大疆、华为、小米的顶尖工程师和产品经理。他们不仅懂技术,更具备全球化视野、品牌塑造能力和用户洞察能力。他们要做的是 DTC (直面消费者)的品牌,而非贴牌的货物。
从行业来看,智能影像企业影石科技上市后市值达到了千亿元, 3D 打印企业拓竹成立六年,估值已超过 100 亿美元。成功的标的出现,给足了想象空间,美元基金们不再犹豫。
“ 一个 AI 硬件公司,可以讲用户增长的故事、数据飞轮的故事、订阅服务的故事,甚至生态协同的故事。 ” 红杉中国合伙人张涵说。在 2025 年的深圳,红杉成为了出手最积极的机构之一。
张涵没有否认市场上存在的竞争,作为红杉种子基金的负责人,他在这轮的布局围绕着 “ 提前锁人、快速交割 ” 。为了迅速抢占优质项目,他们提高了项目的决策速度 —— 最快速的项目从接触到下 TS 仅需两三天。
为避免因流程耽误项目推进,红杉还会用 “ 过桥贷款 ” 模式,先给企业打一笔款,让急需资金的早期团队启动产品的研发。后续再完成正式投资款交割。
《财经》走访了多家深圳智能硬件创业者,他们大多在最近两个月中完成了一轮融资交割,而新的融资已经在路上,2026年上半年就计划完成新的两轮融资。
这样的速度让杜明华(化名)倍感压力。她所在的投资机构,是深圳本土一家颇有实力的人民币基金,管理的资金总额并不小,既有国资 LP (有限合伙人),也有知名企业 LP 。
她于 2024 年末开始关注消费级智能硬件,即便就在本土,却没能 “ 近水楼台 ” 。
杜明华告诉《财经》,红杉、高瓴的决策速度快到一两个星期(实际上三天就行),而她们最快也要一个月。
一个月已经是深圳本土基金中,决策速度最快的了。王乐所在的机构,投资决策时间需要四个至六个月,这个速度在人民币机构里更常见。
在 2025 年 11 月,大疆投资了一家 3D 打印企业 “ 智能派 ” ,这引发了大疆前员工、拓竹创始人陶冶发 “ 朋友圈小作文 ” ,称此次投资更像是老东家对拓竹发起的 “ 火力打击 ” ,而非纯粹的 “ 价值投资 ” 。智能派一下子 “ 走红 ” ,后续两轮融资也提上了日程。
王乐不禁可惜,早在半年前,这个项目就在他们内部过会,那会儿估值还不高,但他们一直没有推进。

摄影/刘以秦
投资决策变快也和消费硬件的行业特点有关,消费硬件产品量产上市后,如果有不错的销量,公司就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,对融资的需求度就会下降。拓竹科技成立了五年,只在早期拿了两轮融资。不少投资人担心,错过早期的 “ 窗口期 ” ,就很难再投进去,因此他们必须抢在早期轮次投进去。
更快的决策速度和更早的轮次,让投资机构之间的竞争 “ 前置 ” 了,而越往前,信息差越明显,深圳智能硬件的投融资变成了 “ 圈层 ” 游戏。
“小圈子”里的游戏?
这一波深圳投资热潮中,投资机构们已经分出等级。第一梯队的是红杉中国和高瓴, 1.5 梯队的是顺为资本, IDG 资本、经纬创投、五源资本、美团(美团战投、美团龙珠)等知名投资机构只能再往后排。
深圳本土的风投机构,在这场热潮中似乎集体失声。杜明华玩笑道: “ 我们相比他们(美元基金)的唯一优势,就是不用坐飞机。 ”
但许多美元基金的投资人,已经搬来了深圳。在 2025 年,张涵就飞了几十趟深圳。另一家美元机构的投资人在 2025 年 11 月搬到深圳,住在大疆附近,过去两个月,他投了七家智能硬件创业公司。
早期投资风险最大,因为无法验证产品是否能 “ 卖爆 ” ,在这场智能硬件的抢夺中,人才就成为了最关键的因素。
一线大机构会紧盯大厂的关键岗位人员,尤其是大疆。他们认为,这些人才大多独立带过完整产品线,在供应链管理、产品定义等方面有过实战验证,创业成功率更高。例如拓竹的陶冶、正浩的王雷,均出自大疆。
投资人们也会通过已投企业的高管引荐、行业朋友搭桥等方式,筛选出有创业潜力的创业者,在他们尚未离职时就建立联系。当这些人才因企业架构调整、外部机会诱惑产生创业意愿时,投资人能第一时间对接,在水下完成种子轮的投资。
前述人民币机构投资人提到,他们也会用这种 “ 盯人 ” 的方式去找项目,但很难竞争过红杉和高瓴,尤其是在第一轮融资。就像投资机构需要快速决策、打钱,创业者在第一轮融资时也需要快速决策,让公司能尽快跑起来,在对蜂拥而来的投资人不熟悉的情况下,选择 “ 知名大品牌 ” 最稳妥,且多数创业者在第一轮融资时不会选择引入太多投资方。 “ 我们只能通过和创业者长期的沟通,让他们在后续轮次里选择我们。 ”
他的观察是, 2025 年深圳的消费硬件领域,多数情况是红杉和高瓴在第一轮融资里抢 “ 领投 ” , “ 顺为也很激进,但有一些创业者会担心顺为背靠小米,未来会有业务竞争 ” ,红杉高瓴会互相加价一轮到两轮,不会再多了, “ 因为几乎没人能跟它们抢 ” 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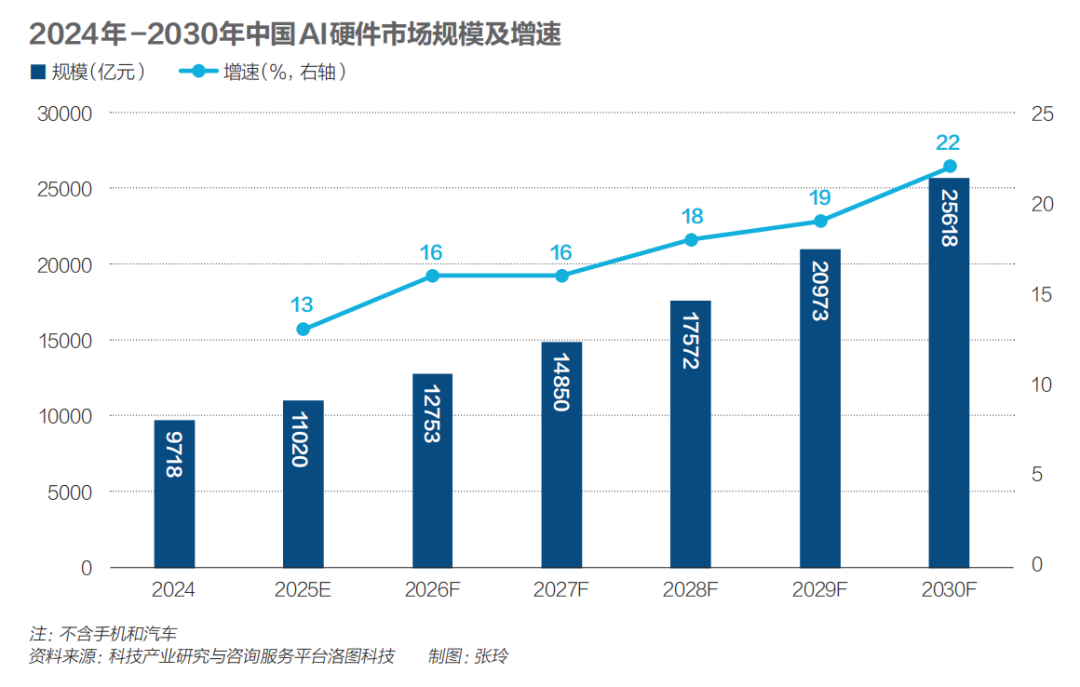
大机构们有自己的人脉网, FA (财务顾问)机构也有自己的门路。
山与资本早在 2023 年初,便开始主动渗透大厂圈层,以 “ 交朋友 ” 的姿态,与大疆等企业内部的大产品经理、业务线负责人建立联系。当批量大疆系、影石系、云鲸系创业者在 2025 年中集中涌现时,山与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批核心项目。
山与的业务经理周淮(化名)告诉《财经》,这类项目他们几乎只定向发给红杉、高瓴、 IDG 、五源等二三十家头部美元基金。 “ (这些)硬件早期项目估值就不低,还特别依赖全球化资源。 ”
而这些基金 “ 对于落地数据完全没有要求,更多还是从人和事的角度上去做判断 ” ,不会像本土人民币基金那样看重短期业绩;决策速度也更快, “ 有的项目两周就基本搞定了所有机构,之后就不再见人了 ” 。
对于创业者而言,这种定向推送也是一种保护。 “ 这些创业者原来在企业里都是大咖,撒网这种方式不太合适 ” ,周淮解释道, “ 撒网式推送 ” 会导致重复沟通却难以达成合作, “ 说白了会把很多人都得罪了 ” 。
而将项目集中推给核心圈层,能让创业者在与 10 家 -20 家机构沟通后快速拿到结果,避免长期 “ 待价而沽 ” 。
杜明华和那几家活跃的 FA 都有长期的联系,交情也不错,但她拿不到 “ 大疆系 ” 项目的推荐。在她看来,投资 “ 大疆系 ” 创业者,几乎变成了一个 “ 小圈子 ” 里的游戏。她早就看清了现实: “ 红杉跟高瓴都在盯大疆高 P 的人,我放弃那条路了,竞争不过。 ”
张涵并不这么认为,他把投资分阶段来看。他们更倾向于在公司还没组建,甚至只有核心创始人时就切入。 “ 第一轮下手比较狠的,主要是我们、高瓴、顺为这些机构。 ” 这个阶段的项目信息相对封闭, “ 我们都摁得死死的,不敢出去讲 ” 。
但到了第二轮,格局就不同了。 “ 从公司发展角度,它需要更广泛的投资人来参与。 ” 张涵解释,第一笔钱往往只够搞定产品,要扩大市场、补充现金流,必须启动多轮融资。更关键的是,创始人也不想让单一机构话语权太强。
这时候,原本封闭的信息会逐渐拉平, “ 第二轮往后就变成市场上公开的了,信息慢慢就对称了 ” 。在这一轮中,美团、五源、 IDG 、经纬,甚至是小红书战投,表现得十分活跃。
随着轮次推进,估值的上涨也顺理成章。多位投资人提到,有些项目连产品都还没有,估值就已经大几千万美元了。
张涵表示,这不是小圈子玩法, “ 每往后走一轮都会扩大一大圈 ” ,早期没抢到的优质项目,在后续轮次中仍有参与机会,只是此时的估值已远非种子轮可比。
这种一步步开放、估值逐步抬升的模式,也成为当前深圳硬件赛道融资的典型特征。
缺位的深圳本土机构
但无论是哪一轮,都很难见到深圳本土投资机构的身影。
“ 你得承认,投资是有 ’ 鄙视链 ’ 的。 ” 一位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告诉《财经》。
“ 真让人生气, ” 杜明华说, “ 但他说的是实话。 ”
首先是估值差异。美元基金的终极目标是通过 IPO (首次公开募股)或并购退出,敢于押注高风险、高增长的故事。他们信奉 “ 投赛道、投人 ” ,可以为一个只有 PPT 和宏大愿景的团队开出天价支票,因为他们赌的是未来的天花板,而非当下的利润。
而深圳的本土机构,大多是人民币基金,他们的逻辑是 “ 先算账 ” :上来就问你今年 3000 万元净利润,未来三年能否翻倍?谈判风格也极为务实。
李永明曾在深圳一家本土大机构工作,他的前老板和创业者谈判时,还没聊到具体业务,一上来就将对方 7 亿元的估值直接砍到 3.5 亿元,双方几百万、一千万地往上加,如菜市场买白菜一般。
在面对需要长期培育和想象力的新兴赛道时,本土机构的反应往往显得迟疑和保守。杜明华举例,去年年终一个热门消费级 3D 打印项目,美元基金给到 18 亿元左右的估值,而她能承受的上限不过 10 亿元。 “ 价差太大了,我们玩不起。 ” 她说。
这已经让王乐十分羡慕, “ 要是我推一个估值 10 亿元还没有营收的项目,我能被投委会骂死 ” 。
其次是决策慢。王乐所在的机构详细地划了 19 个行业小组,每个投资经理都有明确的 “ 行业标签 ” ,比如投材料的,就不能推装备类的;投生物科技的,就不能推先进制造的。公司有 60 多位投委会委员,按行业细分专业,找到对口的评审、协调开会时间,往往就要耗费一两个月。
到了最终的决策环节, “ 正常一个月最多上 20 多个项目,到了四季度冲业绩, 12 月一个月能上四五十个项目,领导们一天开五六个会,累得够呛 ” 。王乐说,项目排队上会是常态,遇上热门赛道的项目扎堆,等排到自己时,市场早已变天。
王乐坦言,不是没看到风口,而是他们无法快速行动。那些智能硬件项目,美元基金已经完成投资,而他们的案子还在预审会阶段, “ 等我们上投委会,项目估值已经从 6000 万元涨到 3 亿元,再想投已经不划算,只能放弃 ” 。
而且一些企业并不愿意在前几轮融资中拿本土基金的钱。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基金大多有严格的回购条款,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有招商的诉求。
多位投资人、创业者证实,在当前的硬件市场上,深圳本土的南山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(南山战新投)十分活跃。据受访者透露,南山战新投可以跟投每一个拿到融资的项目 500 万 -1000 万元,且不要求回购,但他们的一项要求是,企业必须落地深圳南山区,三年内不能搬走。
王乐所在的机构则每年都要对一批企业执行回购条款,走法律清算,在行业中饱受争议。他很无奈,签回购在他们这里是硬性规定。
李永明长期和深圳本地的人民币机构打交道, “ 深圳人民币机构的 LP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政府 ⋯⋯ 至少要保证不赔本。 ” 这决定了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博取高倍数回报,而是保全国有资产。
“ 国有资产流失 ” 是一条高压线,碰不得。也是因为这些国资机构身上背负责任,他们在投资决策上的表现相对更保守。
以某家深圳本土的头部国资机构为例,内部有 “ 奖四罚二 ” 的规定:如果项目投资成功,负责该项目的团队能够拿到投资回报的 4% 作为奖金,但失败了,就要罚款投资金额的 2% 。
多年前,他们曾重仓某家科技企业。项目失败后,相关团队被处以近 2000 万元的罚单,主要负责人一人就得承担 500 万元。这笔罚款从年终奖中扣除,每年年终奖一到账,立马清零。
在 “ 罚二 ” 之外,他们还要 “ 强制跟投 ” 。每位投资经理在项目交割前,都必须拿出真金白银,跟随基金一同投资。这笔钱的意义远超财务层面。它是一种忠诚度测试,更是一种风险共担的仪式。
当美元基金可以轻松地为一个只有算法模型的 AI 团队开出支票时,深创投的投资经理们还在为找不到可靠的回购方而发愁。他们不是缺乏眼光,而是在制度设计上,就被预设为 “ 保守派 ” 。
“ 这是一种悖论, ” 李永明评价道, “ 你不能让它既像政府一样安全,又像市场一样激进。 ”
中国硬科技投资的两种力量
深圳本土投资人们理性地判断,自己将错过这轮 “ 大疆系 ” 的硬件创业浪潮。便如他们 20 年前错过了腾讯一样。原因、结果他们都总结了无数次,但依旧会踏入相似的轮回。
手握重金,坐拥地利,却为何总是挤不进属于自己的盛宴?要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回溯那个中国资本市场尚在襁褓中的年代,去探寻深圳本土资本那深植于血脉的 “ 基因 ” 。
深圳本土资本的故事始于 1994 年。这一年,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(深高新投)成立。它的使命并非今天人们熟知的风险投资,而是为那些缺乏抵押物、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。
其诞生之初,就决定了属性 —— 它不是市场的冒险家,而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,是金融体系的稳定器。它的任务是降低风险,而非拥抱风险。 “ 相当于我们要为企业承担 90% 的风险。 ” 一位深高新投投资人表示。
五年后, 1999 年,为了响应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号召,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(深创投)应运而生。它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政府引导、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机构。
然而,即便名为 “ 创新 ” ,其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浓厚的 “ 硬科技 ” 血液。它的早期成功案例,多是同洲电子这类机顶盒制造商,而非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。
即便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,深创投内部还是会常常提及 “ 我们错过了腾讯 ” 。现在则会提及错过了大疆和拓竹。
 深圳拓竹科技的线下门店 摄影/黄思韵
深圳拓竹科技的线下门店 摄影/黄思韵这并非偶然。国资的投资惯性,是看企业的净利润和市盈率,以及是否符合政策支持的领域。对于一个长期亏损、靠用户增长讲故事的互联网公司,深圳本土机构的决策机制和LP很难理解。
这种以实体、制造、可量化回报为核心的 “ 制造业信仰 ” ,构成了深圳本土资本的第一重基因。它务实、稳健,但面对需要想象力的新兴领域时,便慢了一步。
事实上,无论是深创投、高新投,还是后续逐渐成长起来的达晨、正轩、同创伟业等机构,即便并非完全的国资背景,也受这一重的基因影响。
面对美元基金在 AI 硬件赛道上的快速卡位,深圳本土的投资机构并未陷入恐慌。他们清楚自己的角色和限制,也有各自的生存之道。
王乐和同事们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有一次,他们跟一家企业聊,得知企业已经跟另一家机构处于投资敲定阶段。只见他的同事摊手、拧眉、叹气,一气呵成。 “ 你怎么敢拿他们的投资呢! ” 同事拿出手机,翻出某个企业信息软件, “ 你看看,他们的诉讼案件这么多 ” 。
王乐顿时心虚,要是这个老板搜索他们机构的名字,会发现诉讼案件更多。
有时他们还会扯面 “ 大旗 ” 来站台, “ 我们跟市、区的工信局、科创局关系特别好。 ” 当一个项目犹豫不决时,他们会直接 “ 拉到某些领导,带着处长、副局长就直接到企业里面调研 ” 。他们会暗示老板,可以帮忙解决 “ 消防、环保等卡脖子的问题 ” 。
“ 真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? ”
王乐笑了, “ 当然不能,企业合法合规的程序必须得自己走。 ”
王乐会用调侃的方式吐槽自己的日常工作,而这种调侃的背后,也是一种放松的情绪。 “ 我们比较讨厌追涨。 ” 汇报项目时,领导会问为什么要投,如果他的答案是市场很热,估值在涨,领导并不会心动,反而会厌恶。
陆明华也没有那么急。在争夺大疆系顶尖人才的战场上, “ 我们肯定抢不过 IDG 、红杉 ” 。于是她转换思路,不去追逐最热门的 “ 尖子生 ” ,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找项目。 “ 我们找小米背景的,或是在交叉领域里有独特想法的团队。 ” 她认为,只要判断准确,同样能投出好项目。
如果在一个领域深耕,也能从从容容。
徐清自己就做过 3D 打印项目的创业,做回投资人后,他又投了不少项目。凭借早年的创业经验,能与创始人进行深度对话。这让他能在早期就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团队,并以更合理的条件进入。 “ 有些创始人愿意为我们单独开一轮。 ” 他说。
美元基金与本土人民币基金,在深圳扮演着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角色。
正如张涵所观察,美元基金凭借其灵活性和高风险偏好,能 “ 非常积极 ” 地押注高潜力项目,迅速点燃一个行业的热度。
而本土的人民币基金,则因其国资背景和稳健风格,成为市场的 “ 稳定器 ” 。
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,一家明星智能硬件企业在 2025 年完成了一笔来自深圳某国资的数亿元的投资。行业人士告诉《财经》,这家企业因为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陷入困境,于是写了一封信向深圳的有关部门 “ 求助 ” ,随后就有了后续这笔融资。
深圳本土人民币基金或许会错过最耀眼的明星,却为深圳这个创新生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托底力量 —— 确保即使在泡沫破裂后,仍有坚实的硬科技企业能够存活并继续生长。
“ 我们比较讨厌追涨。 ” 这句话的背后,不是保守,而是一种对城市长期发展的责任。当喧嚣散去,真正决定一座城市产业根基的,往往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明星,而是那些在托底力量支持下,默默生长、穿越周期的 “ 慢公司 ” 。
在深圳南山的灯火下,美元基金也好,本土机构也罢,两种力量共同编织着中国硬科技的未来。
(作者胡苗为《财经》研究员;刘以秦为《财经》记者)
版面编辑 | 陈湘
加
入
群
聊
财经五月花开通读者群啦! 想Mark 最新一手金融热点?想Get有价值的金融行业报道?想与行业大咖共话金融?想参与五月花编辑部茶话会?那就赶紧加入我们吧!
【入群方式】添加群主微信Caijing_MayFlower,邀您入群。
]article_adlist–>

]article_adlist–>
]article_adlist–>
<!-- 非定向300*250按钮 17/09 wenjing begin --> <!-- 非定向300*250按钮 end -->
</div>

